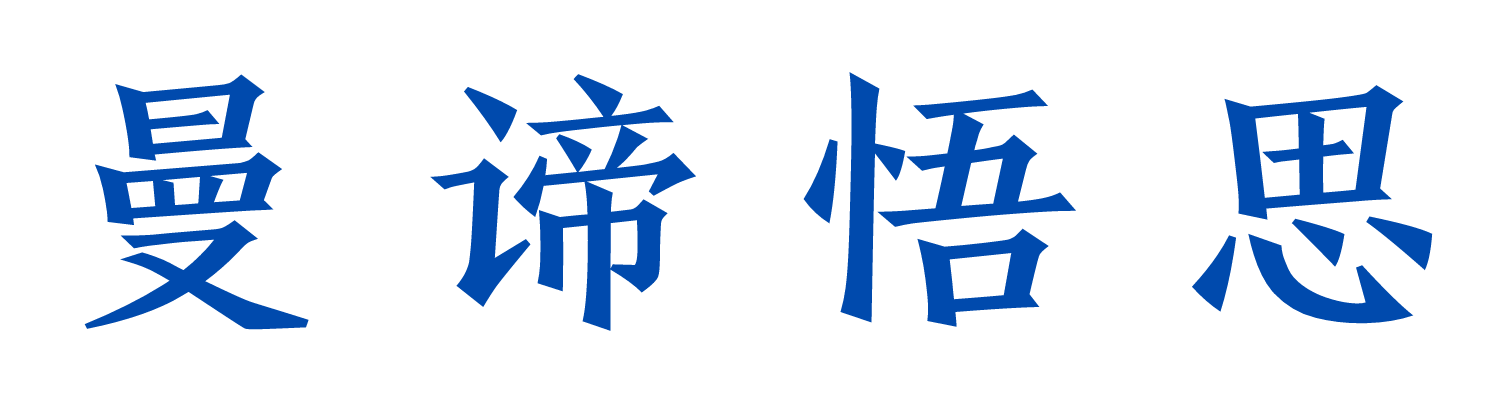涵予:为什么谈论起家庭,你不用一般我们称呼的父母、丈夫、妻子这些称呼呢?
Cico:无论父母还是妻子丈夫,这些都是角色,并不能反映一个人当下的真实状态。
而且每个人都容易困在那里面,忘记大家都是人。角色在社会里面有它的位置,但是如果我们忘了我们都是人而完全进入到角色里,大家会被这个角色所困扰,认为这个角色特别重要。
角色和身份能带来一种位置,一种安全感,但大脑却在里面困着,特别难受,就出问题了。一个人生理上有男女性别的不同,但心理上可以“不男不女”。一旦有了身份标签,比如男性对女性有个期待或一个画面,认为妻子应该怎样做,或者丈夫应该怎么做,那两个人都不自在,关系就一定出问题。
每个人做自己擅长的部分,大家能够相互支持和协作,对吧?这事儿我能多做我就做,那种事他擅长就他来做,没有那种“他应该做什么、我应该做什么”的规则,从人的层面来接触和相处,这样彼此能看到对方真实的样子,才可以及时调整和解决问题。否则一直困在夫妻、父母、孩子的角色里,就很多问题。
涵予:可是这个社会看起来就是这样子的机制,就是这么形成的。
Cico:一个社会的形成都是基于这些概念,谁能够打破它?不是说反对这些东西,反对没有意义,抵触没有意义,而是打破它。
别人爱称什么称什么,但是自己能否意识到自己其实啥也不是,什么角色都不是。这样,无论是跟任何人,包括妻子、丈夫、孩子,才可以有一个完全没有隔阂的沟通和交流。
否则彼此之间的交流其实是角色与角色的交流,大家就完全进入了一个系统,进入了想法的活动里面,他就看不到真正的问题。看不到问题,更谈不上解决问题。
这不光是中国,整个世界都是这样。在这样一个状态里,每个家庭都有不可调和的矛盾,是因为大家都被角色所累,忘了自己是人,也不知道该怎么是个人,戏演惯了之后忘了怎么可能走出戏,回到真实的状态。
涵予:所谓的戏就是脑子里的这些观念、组合。
Cico:观念的组合、角色以及对应的各种“应该是”的画面。大脑总是遵循模仿过去的记忆,执行某个指令,大脑没有在观察,所以观念、文化或意识形态等等这些东西,和各种观点,各种思想体系总在指导人,但人却不去做新的观察,所以有大量的应该不应该。整个社会的运转都是这样子。
涵予:可是观察紧接着就会产生一些想法呀,或者说观察本身是否也属于想法的活动呢?
Cico:观察完全不是一个想法的活动,观察本身独立于想法。有观察的时候想法的活动,和没有观察、纯粹想法的活动,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在基于已有的观点、背景、结论、知识,来去分析它,那这个是单纯想法的活动,没有观察;观察的时候,没有观点、没有背景、没有结论,不被知识所困。那以这个观察为出发点,所对应的想法活动,没有这个中心,没有这个我。
涵予:你可以描述一下这种没有想法的观察是什么样的,比如说能举个例子吗?
Cico:比如说咱们看这个手机怎么观察?
涵予:看到手机马上就会有一些想法,比如说它是什么形状的,什么颜色的之类。
Cico:看到这些想法的活动。我能否看到这些,而不去辨认它?我们能看到大脑思维可能在辨认,在想它的形状、功用、是什么牌子……能否在此刻意识到这个意识活动,而不是即刻跟着这些活动跑。
当我如实看这样一个东西,我可以摸一摸它,我能看到它的颜色,也可以感受它的质地重量,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,这是观察。
就像我们看外面这棵树一样,我能够看到它的颜色,可以摸摸叶子的质地,闻闻它的气味,这些都不是想法的活动。但此刻我一想这树叫啥名字?是什么科?多大岁数了,漂不漂亮?颜值好不好?你看一下子都进入到意识活动里面去了,而观察就是能够看到眼前的事物原本的样子。
涵予:比如认它的颜色不算想法吗?
Cico:你看而不是辨认出是什么颜色。看到那种颜色对视觉的冲击,那种对比,那种鲜艳,那是整个神经系统的感受;但如果想法进来,说“这是绿色”,大脑能否意识到这个过程?而不是即刻进入到想法——进入到绿色的叙事里面去。大脑这么做本身在剥离。
不是说我要去主动怎么做,而是大脑在如实的观察中它会自己分离。
涵予:自己分离?
Cico:对!一方面你在看这棵树的样子,同时留意大脑各种想法的出现,各种辨认的活动。观察到这些,但是不进去,这本身就在松绑,大脑的想法会跟单纯的看东西剥离开来。但如果我们总在抓住那些意识活动,比如绿色真漂亮、树好美,你看意识活动始终会附加在这一层上。
能否看到这一层,同时意识到相关的活动,而不去跟它有这样一个接触?为什么咱们大部分人总在抓住想法?所以想法会一直在延续着,所以一个人始终没办法观察,因为他抓住想法之后,一切都是通过他的想法来看世界。
每个人独特的经历,他的知识,知识的获取,受过的创伤......这些都会扭曲一个人对于世界的看法,就像透过滤镜在看事情。包括咱们刚刚说的家庭角色,妻子、丈夫、父母,也是一个想法的滤镜。所以当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,我们就无法看到彼此,人与人之间就无法看到彼此原本真实的样子。
当大家都在这些角色里,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,但那些问题都是次要问题,而且永远解不完。那一个人能否发力,去看到本质问题,那这些角色对应的问题全部不再是问题。但你看大部分人整天都在解决次要问题。所以大脑能否让相应的意识活动和感受感觉剥离开来,然后让它能够自然止息,该用的时候用,不需要的时候自然地止息。
涵予:所以需要刻意的练习是吧?
Cico:刚开始有意识的练习,没问题,或者说常常去做这种观察,然后警觉到想法出现了,意识到想法的局限。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想法的局限,他会觉得想法可以无限地蔓延扩展,他从中能够感受到满足和愉悦。
当一个人对想法开始有觉察,发现想法的局限,最终大脑可以毫无选择地,没有任何选项地去做这个事情。如果说这东西是个选项,大部分人就不做了;意识到这事情必须这么做,没有选项,没有退路。
涵予:很多很多老师、书籍都在说觉察,我也觉得自己是了解什么是觉察的,我能意识到自己在想什么,能意识到自己的感觉、此刻的情绪、心理活动等等。最近才有一个更清楚的看见,比如说看到有人事情没做好,我看见脑子里会有一些想法出来,会有评判,有情绪,那一刻才意识原来自己完全在这个思维活动里面。我就在想那以前自以为的觉察到底是什么,为什么现在才有这种很清楚的感觉。
Cico:出现一个洞察,突然意识到这些都是一连串想法的活动。
涵予:对,而且这些想法根本没有停下来过,一直在运作。
Cico:像您刚才说的有洞察出现了,就突然意识到了“刚才这些东西都是想法”,那一个人能否有洞察?一个人在这样的觉察中洞察会自然出现,但前提是觉察它不是个选项。洞察是无法去追逐的,无法追求洞察出现,大脑必须得致力于没有任何选项地去观察整个想法的活动,整个想法和感觉黏着在一起的状况。这样做本身大脑自己会把感觉和想法分开,同时大脑会有它的洞察,对自己过往的洞察。
但是洞察不能去追逐,我只能说我打开门,风什么时候吹进来,我决定不了,但我必须打开大门,打开窗子。
涵予:我才意识到大脑的活动是可以停下来的。
Cico:完全可以。
涵予:以前可能只是知道有情绪有想法,而现在发现这些都是想法,它是可以停下来的。
Cico:不是说我忘了什么,而是大脑有一个这样的状态,想法停了。
涵予:但是大脑好像有一个惯性或者说一个恐惧,比如遇到那些具体的事儿的时候,它的运作就是想要有解决方案,就是会持续去想怎么样才能解决那些个问题。
Cico:公司企业的安排,事情的开展,这些具体的事情肯定需要有想法,咱们不是说你不应该有想法,那就走极端了。咱们指的是人在心理层面,他的心理问题,比如创伤,创伤是无法通过想来想明白的。但人很容易去想“我究竟是怎么回事,我为什么不快乐”,结果整个的心理学理论,各种精神分析理论就会来分析你。这是个产业链,而且学来学去就这样,学的越多好像越难受,学的越多问题越多。
涵予:对,是。
Cico:很多理论它本身是有问题的,可能看上去有道理,但是你真正到实际操作层面的时候,很多回路是非常细微的问题,所以心理层面的问题不能通过想法来解决。
涵予:要怎么解决?
Cico:这是一个人需要迅速发现的,当大脑静下来,大脑自己会解决问题,而不是我去解决这个问题。“我”是什么?我是意识活动。
涵予:意识活动跟大脑的区别是什么?
Cico:大脑是整个神经系统的一个协调的中枢,它包含整个的我们的感官觉受,还有各种你无法用语言去表述的那些你可以感受到的东西,但是意识活动是言语、画面、想法活动的集合。
涵予:意识活动等于思考吗?
Cico:意识活动的范围更大,包括人的愉悦、恐惧等等。咱们不是去谴责思考,人可以思考,但思考并不完全仅仅凭想法来思考,你的思考一定来自于你的整体感知,思考才可以适得其所。如果只是想法的活动,整出一套什么哲学或各种的观点……
涵予:就很单一偏颇。
Cico:对,全是意识活动,和身体脱节,所以那个东西就容易停不下来。
涵予:刚刚说大脑自己能解决那些创伤问题。
Cico:对,这个是最神奇的地方,也是大部分人不信的地方。
涵予:可能每个人对大脑这个词的理解不一样。
Cico:那咱们就换个词,因为语言并不重要,咱们换个词,比如整个神经系统。
涵予:神经系统。
Cico:神经系统遍布全身,大脑也是其中的一部分,但是意识活动只是想法的运动,是机械的东西,但你看我们整个人的生活,整个社会的运转都是基于那一小撮意识活动。
涵予:所以你的意思是当想法止息下来,所谓的受伤感和创伤,整个神经系统或身心整体,它自己能修复。
Cico:它修复,然后重生。但是一个人要致力于让大脑静下来,而不是整天去解决他认为是问题的那些心理问题。每个人都困在他自己认为是问题的那些心理问题里面,想要通过他的想法,他的意志去解决这些问题,结果永远解不了。
涵予:这也就是“无为而为”。
Cico:对。就是脑袋的意识活动不再去“作为”,不要去解决去做那么多事情,反而整个神经系统在运作、在解决这个问题,这就是理解。
//
对话者:
涵予,归心之旅主理人
Cico,曼谛悟思创始人
链接: